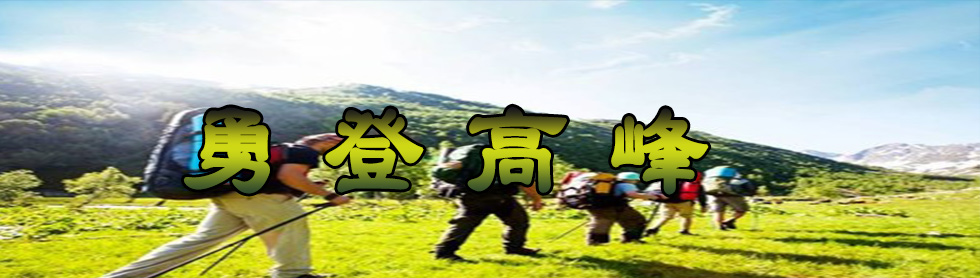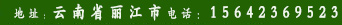|
《卷耳》牵涉到一桩纠缠不清的“谜案”,那就是:《卷耳》里的“我”是谁?年来,很多学者都试图提答这个问题,但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参与进来的学者大名鼎鼎:毛亨(战国),焦贡(西汉),郑玄(东汉),孔颖达(唐),朱熹(宋),方玉润(清),程俊英、周振甫、高亨、余冠英、钱钟书(现代)… 01《卷耳》诗、译与争论焦点 《诗经·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程俊英版白话译文:采呀采呀采卷耳,不满小小一浅筐。心中想念我丈夫,浅筐丢在大道旁。登上高高土石山,我马跑得腿发软。且把金杯斟满酒,好浇心中长思恋。登上高高山脊梁,我马病得眼玄黄。且把大杯斟满酒,不让心里老悲伤。登上那个乱石冈,马儿病倒躺一旁。仆人累得走不动,怎么解脱这忧伤!注:这个版本其他的学者可能有不同意见。争论焦点焦点①:采卷耳的人和登山的人是同一人吗?按程先生译文,采卷耳的是女子,她是采了卷耳又去登山怀人吗?也有人认为采卷耳的是男子,那么是他征发在外,带仆人采卷耳又登高怀人?焦点②:如果采卷耳和登山的不是同一人,那么怎么会出现两个“我”?——一个是真实的我,一个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么,采卷耳的是真实的我,还是登山的是真实的我?焦点③:会不会是两个人在不同的空间同时出现?一个采卷耳,一个登山?可能吗?02先秦汉唐经学家的理解 孔颖达是唐代经学家,孔子31代孙,他在战国经学家毛亨《毛诗正义》传、东汉经学家郑玄《毛诗正义》笺的基础上著有《毛诗正义》疏,三者的思想大致是一以贯之的。孔颖达认为:《卷耳》的“我”共3人,甲是周后妃某,乙是周使臣某,丙是周王某。丙和甲是夫妻关系,丙和乙是君臣关系。整首诗的作者是后妃“我”。首先,他认为第一章“我”是后妃。从采卷耳,连浅筐也装不满写起,表现后妃忧心忡忡,想着君王能任用贤臣。“嗟我怀人,寘彼周列”中的“周列”后世的理解是“大路”,而他理解的是“周朝廷的位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才认为这里的“我”是周王后妃的。其次,他认为第二三章的“我”有两个,骑马登山的是使臣,喝酒伤心的君王。他的思路是后妃希望贤臣到周,贤臣果然就到了,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去出使。国君感念臣子辛苦,内心忧伤,想着臣子回来后举金罍、兕觥感谢他。怎么推断喝酒的是君主?因为“人君黄金罍”。最后,到了第三章,他认为又变成了后妃的感慨:使臣为君主辛苦效命,仆马皆病,因而感动、怜悯。悦华认为,郑玄、孔颖达等做的是“经人解经”的工作。他们不会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而是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因此满眼是君王后妃,圣主贤臣,这也是后世学者多不认同的原因。但带有启发性是,孔颖达认为叙述者是后妃“我”。全诗都是后妃在吟唱给君王听的,她先为不得贤臣而忧伤,又设想贤臣到来后非常辛苦,建议君主好好对待。所以其中的“我马虺隤/玄黄”的“我”是“我臣”的简称;“我姑酌彼金罍/兕觥”中的“我”是“我君”的简称。03清代学者方玉润等的认识 方玉润,清代学者,《诗经》研究大家,著有《诗经原始》。他一反毛颖达的认识,在《卷耳》的阐释上对后世学者有特别大的启发。方玉润认为《卷耳》中的“我”指两人,一是采卷耳、饮酒的思妇“我”,一是行役登山的丈夫“我”。而诗的叙述者是思妇“我”。首先,他打破了毛颖达的“后妃之志”说,认为《卷耳》为“妇人念夫行役而怜其劳苦之作”。证据①:从训诂角度看,孔颖达们所说“周列”意非“周朝廷行列”,而是指“大道”。证据②:从逻辑角度看,遵道采卷耳,“岂后妃事也”?由此可见,第一章乃思妇因采卷耳动怀人之念,采不盈筐弃之路旁,有“一往情深之慨”;而后三章从对面著笔,想像丈夫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方玉润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否定了“经人解经”的做法,认为“后妃之志”是“腐儒”断章取义、胶柱鼓瑟之解,将“后妃”置换成“思妇”。然后他以文学的眼光看《卷耳》,认为后三章在写思妇想像中的丈夫,是一种从对面着笔的文学方法。这样,他成功地将《卷耳》拉下“神坛”,并“抹掉”了孔颖达解说中的一个使臣“我”。需要说明的是,余冠英、程俊英等现代学者对方润玉的学说有继承,也有扬弃。以余冠英为例,他认为: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第一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余冠英《诗经选》)程俊英也有类似的说法。比较余、程和方润玉的说法,区别仅在于前者认为二三四章全是思妇的想象,后者认为二三章中登山的是征夫“我”,而借酒浇愁的则是思妇“我”。04现代学者钱钟书等的新解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一步对《卷耳》的叙述者、诗中之“我”做了耳目一新的理解。他的结论是: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先,他认为孔颖达们的“后妃说”迂阔可哂——哪有“求贤”而几于不避嫌的后妃?其次,思妇称自己为“我”正常,设想丈夫时再称“我”以模拟丈夫的口吻则“葛藤莫辨,扦格难通”——既混乱又矛盾。这表明方玉润们第二~四章言思妇设想丈夫行役之状属判断错误。第三,与其说二~四章是思妇为夫代言,还不如说诗的作者在同时为思妇、征夫代言!换句话说,诗的作者既不是思妇也不是征夫: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最后,为表明论证的正确性,大量引用中西方诗文以作类比,不仅指明这种“两头分话、双管齐下”的结构方式大量存在,更指明《卷耳》为最古老的一个。钱钟书先生观点的创新性在于他引入了“代言”的概念,一反以往后妃“我”、思妇“我”即是诗歌作者的看法。这样,诗中的“我”无论思妇还是征夫,都只是用第一人称指称的对象而已。这样一来,解决了《卷耳》里关于“我”的纷乱头绪。值得一提的是,北师大李山教授在钱钟书先生的基础上又提新见。他以新发现的材料孔子评诗“《卷耳》不知人”入手,认为《卷耳》采用的是一种歌唱方式,第一章为女子所唱之词,第二、三、四章,则是男子的唱词。(悦华认为第四章理解为合唱之词亦可)这样,对钱钟书先生观点做了很好的补充。对《卷耳》的异见,上面具有典型性,除此之外,还有“我”为思妇(或征夫)一人(“我”即作者),《卷耳》为两个断章拼凑等等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通过对《卷耳》纷争的论述,悦华一方面觉得“诗无达诂”正是诗之规律,另一方面也看到时代的变迁在诗歌阐释学中的巨大作用。一篇《卷耳》先由后妃唱,再到百姓唱,先是教化之声,后是文学之声,这分明是变化着的时代之声!对于《卷耳》中的“我”,您有什么看法,欢迎交流。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ylinedu.com/dsjq/16223.html |
争论2000年的卷耳谜案我是
发布时间:2024/11/29 20:46:16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五一户外运动装备怎么选登山必备物品清单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