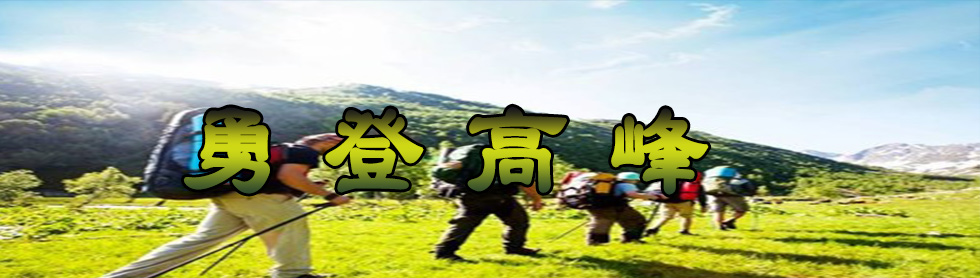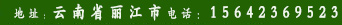|
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index.html 小编按: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作者简介见文末。原文载于《地球奥秘的探索者》,于洸主编。经原作者授权,在此重刊,以飨读者。 米士,著名变质岩石学家、构造地质学家,生于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动荡,一生大致分三个阶段,跨越世界三大洲。早期,在德国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施蒂勒,受哥廷根大学名师们的熏陶,打下了构造地质学和变质岩石学的坚实基础。中期,受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迫使他辗转于华南和西南,但他坚持研究,涉猎较广,特别在地层、构造和变质造山带等方面有许多建树。后期,二战结束后,移居美国,是美国西北部地质构造研究的开拓者。米士从小练就的水彩绘画和攀缘登山功底,在其后学术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讲课生动,内容丰富,指导了多名博士、硕士。他重视实践,强调野外工作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值得学习和传承。 一 米士(PeterHansMisch,-)年8月30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乔格·米士(GeorgMisch,-)为哥廷根大学(GottingenUniversity)哲学教授,其外祖父狄尔泰(WilhelmDilthey,-)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米士从小聪颖好学,大器早成,5岁学习水彩画,6岁练习滑雪,10岁上山采化石,14岁时就开始了严格的登山训练。从小就培养了热爱自然、探索未知、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强健了体魄,为他日后在艰苦环境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生受益。米士孩提时,就特别着迷于化石和岩石,一次户外活动,巧遇著名地质学家施蒂勒(WilhelmHansStille,-)的一些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米士对地球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走上了地质之路。作为“地质神童”,米士23岁就获得了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导师正是米士仰慕已久的大地构造学家施蒂勒。做博士论文期间,米士兼任助教,协助指导高年级学生在欧洲阿尔卑斯造山带野外实习,进行地质填图。当时著名岩石学家、地球化学家戈尔德斯密特(VictorMoritzGoldschmidt,-)和科伦斯(CarlWilhelmCorrens,-)等,也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米士特意选修了变质岩石学课程,为他日后运用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知识,研究变质作用在造山带中的作用和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地质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脉中部一个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变质作用。做论文时,他干脆带上睡袋,住在山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米士是施蒂勒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日后还是施蒂勒的得力助手。年完成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米士地质科学与登山运动紧密结合的特殊背景,受到德国喜马拉雅登山考察队首任队长WillyMerkl的青睐,他应邀加入科学考察队,于年赴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境内,实地考察南迦帕尔巴特(NangaParbat)山及周边地区的岩石和构造,开始酝酿了他许多年后才发表的关于花岗岩化的论说。考察中遇到大风和暴雪,一些队员被困牺牲。米士和另一名队员虽作了顽强的努力,但也未能成功地到达高山营地。考察不能继续进行了。 图1米士照片(右一),拍摄于s,图片由米士学生GregaDigges(中间女士)提供 返回德国以后,他开始研究考察带回的材料。然而,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断升级,变本加厉。作为路德教的教友,米士了解到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血统使他的家庭安全受到威胁,他突然感到自己并不属于德国,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生他养他的祖国。年,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Hanna)到中国传教。离开德国时,他拒绝了德国纳粹要他上交考察资料的命令,将野外记录、薄片、小块岩石标本随身偷偷带出国外。从此以后,他基本上切断了自己与德国文化的联系,甚至与老朋友讲德国语都是带有很大的勉强。 二 米士的导师施蒂勒将他介绍给时任中国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朱家骅。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施蒂勒是他的老相识,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便介绍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两广地质调查所研究员。在那里他有了一个中文中字——米士,据传这个名字也是朱家骅给他选择的。从年秋季起,在中山大学,米士主讲普通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质测量等课程。其中,普通岩石学为地质、地理两系学生合上。年七七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华北,魔爪逼近广州。年10月,中山大学被迫迁离广州,米士妻子因病携女儿回德国,不幸的是他妻子在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theHolocaust)中遇难。(女儿16岁时,才从德国到达美国,在西雅图与阔别15年的父亲相见,这是后话。)中山大学于年2月抵达云南澄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学。杨遵仪教授任系主任,米士主讲的课程有: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区域变质及野外地质实习等。年秋,滇南物价暴涨,师生生活更加困难,中山大学于年7月从澄江迁至粤北坪石,而米士则留在云南转至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年夏,米士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米士也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成员,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主要讲授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地质测量等课程,还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新课程:区域变质作用和欧洲造山运动。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构造地质学课程还编有英文讲义,由学生组织力量油印出来。著名学者刘东生先生回忆说:“米士教授不但知识渊博,上课生动,他孩提时的绘画功底,使他黑板上的地质素描十分精美,而且常把登山器械带入课堂,给学生示范攀缘技巧,使学生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大地构造学和区域变质作用研究精深,课程中涉及地槽、地台、地壳变形、花岗岩化、混合岩化等理论问题,将最新理论和他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在他的培养下,许多学生毕业后立即就可以独立进行地质制图和地质调查工作。他所讲授的课程和在云南西部从事的区域变质作用的研究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和年轻教师的热情。例如,张炳熹和池际尚在美国的博士论文、董申保在法国的博士论文、马杏垣在苏格兰的博士论文,都是讨论区域变质作用的。他们返回中国后都任教授,开展科学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区域变质作用的研究。陈梦熊毕业后到西北工作,对兰州黄河边出露的皋兰系变质岩十分感兴趣,发表了他在西北工作的第一篇论文《甘肃中部的变质岩系》。 米士擅长野外地质,功底较深,观察敏锐,填图迅速,素描图和信手剖面图画得准确、美观。这些长处给学生以很大的教育。在野外教学生如何填图时,他几乎把星期天都花在与学生一起在昆明市的边远郊区工作。每到地层交界或构造变化等关键部位,就停下来让学生自己观察、讨论,最后他再讲解,边画边讲,给学生的印象特别深刻。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日子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米士和他的学生在野外也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他们睡在农民的小茅草房里,或已经毁坏的破旧房屋中,吃的是白水煮面。但他从未报怨过,而且很乐观,经常和学生开玩笑,因而在学生中造成一种欢乐而朝气蓬勃的气氛。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到抚仙湖畔的澄江县实习,爬完一座石灰岩形成的小山后,在湖畔休息。米士突然说;“我有一个问题要考一考诸位,请大家注意,那边近岸湖水中的一块灰色“露头”是什么岩石?一位同学立即回答说:“石灰岩”,有些同学也附和。米士建议那位同学亲自去打一块标本来。那位同学充满信心地将要接近那“露头”时,那块“岩石”却出人意料地摆动起来,再走进一看,原来是躺在水里的一条大水牛,大家不禁哈哈大笑。米士教授最后笑着说:“做地质工作,光用眼睛在远处看是不够的,必须到跟前,用铁锤打下标本,仔细观察后,才能做出正确结论”。听完这番话,大家感到深受教育,从此以后,在野外调查时,都要养成先打标本实地仔细观察的好习惯。 米士在云南期间的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也很丰富,他关于云南东部震旦纪地层学、石炭纪铝土矿床、红层、海相三叠纪的研究以及滇西上二叠统(乐平统)的发现都是卓有建树的。发表了《云南构造史》()、《滇东昆明区之石炭纪岩相并兼论铝土矿之生成》()、《滇西晚二叠世乐平统之发现》()、《云南西北部二叠纪含类岩石》()等论文。他关于云南东部震旦纪地层学研究,为地层对比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也是对扬子江三峡震旦系典型地区剖面的一个补充。提出的“澄江运动”和“晋宁运动”的两个术语至今仍在中国地质学界使用。当他在云南的西北部苍山——金沙江——石鼓地区工作时,通过艰苦细致的野外观察,他提出了“红层变质作用”和“次生衰退变质作用”的概念,虽然他的假说并非完全正确,但这或多或少激励了后来的研究工作。根据他从西至东地质构造的观察,他总结了新造山变形的阿尔卑斯-德国型和震旦型之间的过渡关系。他开拓了云南西部新动力变质作用和阿尔卑斯造山作用的研究。震旦型是根据云南西部的证据对施蒂勒分类的一个补充概念。当他研究震旦纪和石炭纪地层时,还注意了震旦纪磷块岩和石炭纪铝土矿的应用方面,推动了后来的勘探工作。对喜马拉雅西北部和云南西北部地区的“岩基范围的交代变质作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三 年夏,米士离开中国,先访问印度,在那里遇到印度地质调查所所长D.N.Wadia博士,然后去了美国,先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妹妹,并开始研究他在中国采集的上古生界和三叠系化石。当生活在旧金山地区时,结识了聪明活泼的妮可·罗森塔尔(NicolettaRosenthal),相爱结婚,后来妮可还成了米士事业上的有力助手。年,米士遇到了华盛顿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古得斯皮德(GeorgeEdwardGoodspeed),古得斯皮德是一个热情的花岗岩化论者,他邀请米士到他们系工作。相同的学术观点,使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米士接受了邀请,在解决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之后,转到华盛顿大学任教,移居西雅图。他最后找到了一个家。年,米士加入了美国籍。 在华盛顿大学,他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野外地质学、变质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现在称大地构造学),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区域地质学、欧洲及东南亚大地构造以及变质过程。他是一位鼓励型教师,激发许多学生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米士的传奇经历、浪漫人生、人格魅力以及志同道合的同事,吸引了多位青年聚集在他的麾下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开展地质研究,学生的研究遍及北美西北部、加拿大、阿拉斯加、内华达东部、英国、非洲及南北极等地。他要求研究生每周准备一篇论文,如果学生没有很好地准备,在每周的论文交流会上会受到严厉批评。米士会仔细地检查学生的薄片,提出问题,以肯定该生没有遗漏重要的矿物和构造。对论文逐节逐字进行审阅。他灌输思想上和写法上严谨的作风,的确教出了一批很好的研究生。他的许多学生是滑雪运动员或登山运动员,为了让学生在附近的滑雪场进行“下坡研究”,他们在冬季学期的星期四不安排课程。在他的指导下,超过名青年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晚年,有时他怀疑是否为指导学生牺牲了太多的研究时间,然而,最终他认识到,学生们在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功和有影响的地位,充分证明了他的成就。 关于花岗岩的成因,普遍认为是岩浆侵入形成的,但面对巨大花岗岩体如何侵入、侵入后原来的岩石去向等难题,结合混合岩和混合花岗岩之间的连续变化等现象,有学者提出了花岗岩成因的“花岗岩化说”,认为花岗岩是通过深变质作用在原地产生的。由于米士广泛的考察和攀缘经历,使他成为“花岗岩化说”的铁杆拥护者。他认为,花岗岩主要不是火成成因,相反,是变质作用旋回的最终产物,即,从泥岩—页岩—板岩—千枚岩—片岩—最终到花岗岩。虽然花岗岩化假说一般被抛弃,但米士的论文推理论证仔细,表述透彻,这些都是他的论文特征。 在美国地质学会(GSA)的资助下,年,米士开始他对美国西部北喀斯喀特斯(NorthCascades)地区前第三纪结晶质岩系的开拓性研究,这是一项花费了他整个余生的任务。当时,这个崎岖不平、灌木丛生、难以接近的地区在地质学上几乎是一个空白。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士已完成了这个区域大约km2面积的野外地质填图,年发表了《华盛顿州北喀斯喀特斯大地构造演化;西科迪勒拉格架的历史》一文,这是他和在这一地区工作过的他的研究生调查结果的一个概括和综合,概括性地论述了该地区主要的逆冲断层、高角度断层及变质事件和深成岩事件。他认为美国西部北喀斯喀特斯地区山脉的形成,经历了沉积、火山、变质等作用。最后受东西挤压,形成了南北向的造山带,造山带两侧强烈变形、变质的地层分别从东、西两侧逆冲到中部弱变形、浅变质岩石地层之上,形成对称的逆冲和褶皱构造(图2)。虽然现代地质年代学、更精确的地质填图、按照板块构造学说重新分析这一地区,需要对米士的工作重新解释,但现代研究大都证实了他的一些基本结论,他对喀斯喀特斯的研究仍然是这个地区未来工作的基础。 图2美国西北部北瀑布区构造横剖面,示双向对称的褶皱和断裂构造(据USGS略改) 米士对区域地质的另一些主要贡献是在大盆地区。20世纪50年代,他与JohnHazzard一道,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石油协会(UnionOilofCalifornia)的研究顾问,对大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内华达州东部、犹他州西部以及爱达荷州南部进行了地质填图,在兼有区域性发育的变质岩和低角度断层的复杂地域,从事区域地层和构造的研究。这些构造是今天所称的变质核杂岩。虽然米士把这些构造解释为典型的压性褶皱逆冲体系,但他仔细的填图和描述却预示着这一课题内现代思想的出现。年,当美国地质学会把《科迪勒拉变质核杂岩》专著献给他时,米士深感荣幸。此外,他还远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沃希托河(Ouachita)流域的山脉地区进行了研究和填图。 年至年,米士还兼任Bechtel公司发展斯卡吉特谷(SkagitValley)地区核电站可行性论证的顾问,以及美国石油地质学家联合会会刊(AmericanAssociationofPetroleumGeologistsBulletin)的副编辑。 米士对构造地质与岩石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曾担任过美国地质学会主席()职务,并是美国矿物学会、地球物理联合会、伦敦地质学会的会员。 年米士在华盛顿大学退休,退休后继续地质研究,直到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于年7月23日去世。 米士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水彩画家(图3)。他一生作画无数,大部分收藏于地下室,鲜为人见,用镜框挂在墙上的仅有几幅:北喀斯喀特斯的山峰,内华达沙漠的日落,还有湖泊、宝塔以及中国的海岸与浪花。 图3悬挂在华盛顿大学地球科学系办公室内的米士水彩画像,身后的山水是米士本人画的水彩画(绘画人:DeeMolenaar) 米士一生,遭遇多次战争和社会动荡,饱经风霜,历尽坎坷。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科学的追求,是他战胜困难、勇于面对挑战的力量源泉。 作为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登山运动员、滑雪爱好者和水彩艺术家,米士十分强调实践,重视野外工作,并将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紧密结合,这是米士科学研究的特点,是米士成功的“秘诀”,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瑰宝”,十分值得学习和传承。 米士的中国学生和地质学界的朋友十分怀念他,其中许多是杰出的地质学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米士与这些地质学家通讯联系,有些地质学家还访问了他的家。鉴于他对中国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贡献,年,中国地质学会去函邀请他访问中国,作为一位荣誉来宾参加中国地质学会60周年庆祝会。但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他未能满足以前的中国朋友和学生的这一诚挚期望。 年8月,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美国华盛顿大学地质科学系约瑟夫A·万斯、中国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李文达著文《纪念彼得·米士教授》。 参考文献(略)。 本文作者张珂教授 作者简介张珂,安徽凤台人,北京大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新构造运动和地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是一位极具文采的地球科学家。 长按
|
多采的人生著名地质学家登山运动员水彩
发布时间:2021-6-29 12:24:03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夏天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爬山涉水运动
- 下一篇文章: 大型品牌工厂特卖,裳品仓新塘摩丽多店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