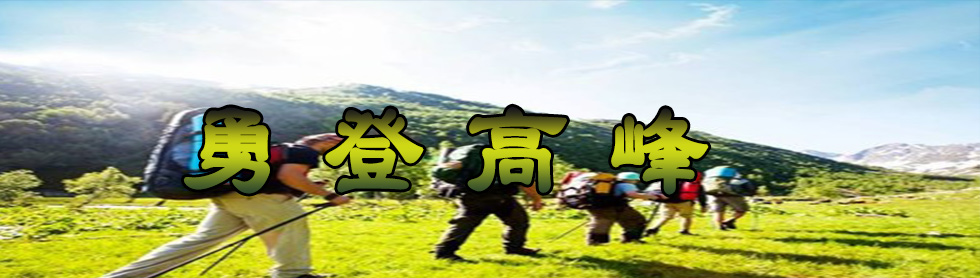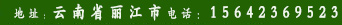|
在世界河流大家庭里,把莱茵河认定为一条世界级的大河在许多指标上似乎都有点“勉强”,比如莱茵河全长仅公里,只有长江的1/5;流域面积22.4万平方公里,是长江的1/8。但有赖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和它流经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河流,年运输量达到3亿余吨,在有些年份还超过了长江! 莱茵,在公元前4世纪这里的居民克尔特人的语言中,是“清澈明亮”的意思,但这条清澈明亮之河也因工业革命蒙羞――工业革命之后它长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但是经过流域各国的治理,又恢复了两岸美景如画的景观。泛舟河上,仿佛不再在空间上移动,而是在时间上移动――在欧洲的数千年历史中穿行,上千年的古堡与现代摩登建筑交替辉映,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莱茵河也曾是欧洲最大的战场,从拿破仑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德、法两国长期以此为界开战,共计有万人战死在莱茵河畔。欧洲人谈起莱茵河,马上会联想到德、法之间的民族恩怨,曾怎样地波及了整个欧洲。但是,莱茵河始终没有臣服于某一个强权。19世纪初流域六国就开会商定从莱茵河到北海的航运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这为莱茵河的流域综合管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今日,流域各国通过多种国际机构进行共同管理,真正实现了与一条河流的共同繁荣。以前几次出差都曾从莱茵河畔匆匆经过,却无缘好好一亲芳泽。年9月,得到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的资助及世界自然基金会总部的邀请,我开始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莱茵河之行,希望能真正揭开这条欧洲大河的神秘面纱。 惊魂阿尔卑斯从法国西部擦着意大利的边境进入瑞士不久,大自然构架的边境线远比人设立的更为明显:山势忽陡,灰白色的穷崖怪石盘空,随着车的驶动,远处的雪峰忽隐忽现,大自然的油画布上顿时色调苍茫。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圣高特山,这是莱茵河的源头之一。我们在荷兰租的一辆大众车一直行走顺畅,它现在开始用沉重的喘息声告诉我们:你们进入“欧洲屋脊”阿尔卑斯山区了。九月的阿尔卑斯色彩渐趋单纯,除了集镇附近偶尔有色彩丰富的植物,白色逐渐统治了一切。地图上显示到圣高特山要经过Furkapass(福卡隘口),附近还有许多这样的“隘口”标志。但两天后在Furkapass的一次惊魂经历,让我永远记住这次莱茵河源之旅的每一细节。随着离Furkapass越来越近,感觉像进入了青藏高原,不知不觉,车窗外开始飘起了细碎的雪花。虽然这里海拔只有多米,但因为纬度很高,气温、景致与同季节的西藏无异。Furkapass原来是一个隧道,隧道口前排了长长的车队,却都是人去车空。等车停稳一看,两边的小咖啡屋里人头攒动,原来都到房间里补充热量去了。看来这里还要等很久,我们也下了车,按指示到一个小亭子里买了票,站在路边呼吸着寒冷却清新的山风。暮色渐起,通行的铃声忽响,我们回车坐好,正在纳闷前面的车怎么不动,突然,我们脚下的“大地”动了起来,而且是飞也似地向前移去,我们的车不断后滑,两边都是万丈悬崖,我们来不及发出惊恐之声,外面又是一片黑暗!车停止移动了,惊魂乍定,一车人才回过神来,原来我们的车停在一块长长的钢板上,所有的车都是由一列火车拖着这块钢板穿过隧道。因为我们的司机疏忽没有拉好手刹,结果在列车启动的瞬间我们的车就开始后滑。幸好甲板两侧有栏杆,不然我们就葬身阿尔卑斯了!也幸好我们是最好一辆车,不然后面车里的人恐怕更吓得不轻。我不想过度渲染当时的情形,出了隧道后却一直在想,为什么瑞士人要这样设计?直到第二天与一个当地人聊起来,他告诉我,这是为了严格控制人进入瑞士的高寒地区――也是瑞士生态脆弱地区,包括莱茵河源头区的一种手段。我不由地佩服瑞士人的匠心,肯定在开凿这个隧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计划,而地图上那么多Pass正好围成一圈,让瑞士环境最脆弱的区域安居在清静之中。而阿尔卑斯正是用这种方式,告诉许多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来到这里、在这里行走并不是那么容易。当晚,我们住在一个叫安德马特的小镇,再过一个多月这里就开始大雪封山了,小镇的居民将在此度过半年左右的幽居生活。除了登山客,小镇上居民寥寥,而且都是老年人居多。我们住在一家叫“太阳神”的家庭旅馆,从窗口外望,家家户户门前装扮的鲜花在街灯中异常鲜艳。 第二天清晨起来,大雾,我们驱车去寻莱茵河源。昨晚与房东聊后就知道凭我们的装备(实际上没有带任何登山装备),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达莱茵河起源的冰川脚下。我们只能沿着一条条雪水融化形成的涓涓细流,看它们怎样汇入到小镇旁的一条小溪之中,而它像一个不断发育的巨人,逐渐在下游形成全长多公里的西欧第一大河。在莱茵河源地区行走,会讶异于它的极致的宁静与古老,仿佛回到几个世纪前的欧洲古国。所有的人都不慌不忙,神色自若,用简单地英语述说他们的简单生活。这里也是全欧洲仅存的仍在使用古拉丁语的一个地区,当地百姓仍然顽强地卫护着这种语言,并且一次次要求州政府立法将它变成官文语言。我们还碰到一对从苏黎世来的夫妇,在这里建了一座木屋,以雪山为背景,劈柴烧火,炊烟袅袅,恍入仙境。毕竟是生态脆弱地区,安德玛特往下不远,我们在一个村庄外也看到严重的泥石流遗迹,就发生在几年前,整个村庄被冲去一半,幸好事先有预报,没有人员伤亡。和一些当地人谈起来,他们对瑞士及全球环境的整体退化还是深表忧虑,源头的冰川在缓慢萎缩,几十年前修的一批大坝也慢慢显示出其负面影响,而最严重的还是旅游带来的冲击。 海德堡的蓝 过了瑞士沙夫豪森的莱茵河大瀑布,就进入德国境内。先是驱车顺流而下,然后乘船逆流而上,所经停的点中,与海德堡只有短短半小时相遇,竟几乎垄断了整个莱茵河中游的记忆。进入德国境内,高速公路基本与莱茵河平行,只是偶尔从河的左岸切到右岸。过了卡尔斯鲁厄,前面出现一个路牌,直指十几公里外的海德堡。这时金色的夕阳已经逼近了天际的山峦,而直觉告诉我,它即将沉下的方向就是海德堡。十几分钟后,我们站在海德堡内卡河(莱茵河支流)大桥上,感叹不虚此行。夕阳迅速落到圣灵山后,内卡河上漂浮起神秘的蓝,将对面的圣灵山,将无数座大小错落古堡,将内卡河面上往复不断的划艇,将河岸上休闲的人群全部包裹其中。 拾步下桥,站在河岸上却又是另一种看河的角度。最让人欣喜的是看到了成群的天鹅和野鸭,就在河岸一片小树林旁游弋,对身边的人丝毫不惧。随着华灯渐起,这些野性的生灵被勾勒成一幅美丽的剪影。在西欧,实际上四处能见到这样的场景。鸟与人能够如此之近,这似乎有违我们在国内的常识。欧洲也有很悠久的狩猎传统,但从殖民时代到工业革命,扩张几乎耗尽了本土上的所有自然资源。欧洲的保护人士反而非常艳羡中国仍然有丰富的原生态,而西欧几乎完全是重新人造的,物种的多样性比较差,许多独特的物种消失了就永远不再回来。我们途中看到不少鸟,但种类很少。而大型的动物只有在荷兰看到了一群野牛和野马,都是从苏格兰重新引进的,已经基本失去了野性。内卡河经海德堡马上就汇入莱茵河干流,往西北不远就流到美因茨,从美因茨到科隆是莱茵河黄金游线,中间经过宾根、科不伦茨和波恩等一大批古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两岸及河中礁石上的古堡与葡萄园是最主要的“卖点”,又被称为“古堡之路”或“葡萄酒之路”。几天后我从科隆出发,逆流而上,第一夜宿在科不伦茨,次日下午才到宾根下岸。这两天惠风和畅,阳光温柔,很适合河上航行,游船无不客满,但走了半天,我就觉得审美疲劳,古堡密度之高,实在令人惊叹,但因为缺乏相应的背景文化,却让我总觉得对这样的景点隔了一层,慢慢地就分不出区别了。而海德堡不同的是自然风光与人文积淀的极佳融合,圣灵山上的古堡与内卡河的行人成为一个整体,是活着的文物。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海德堡大学至今仍是德国最著名的大学,是德国诸多学科、包括哲学的一个核心。而大哲学家荷尔德林就在圣灵山上度过一生,他边思考边散步走出来的“荷尔德林小径”至今有无数人去追随。在游船上,只能跟着导游虚拟想象曾有“七位少女”在罗累莱山崖上歌唱,她到底唱了什么样的歌,我却实在无从想起,但荷尔德林在圣灵山上衣裾飘飘场景却始终如在眼前。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心中,海德堡能比下了整个莱茵河黄金游线的原因吧。船行时我一直在注意莱茵河的水质,莱茵河是一战后德国工业发展的根本,为鲁尔、洛林等大矿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也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污染,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莱茵河的污染达到顶峰,被誉为“欧洲最浪漫的臭水沟”,短短几十年的治理,莱茵河水质究竟怎么样了呢?但是一路所见,水无不清澈见底。在科不伦茨我们造访了莱茵河国际委员会,了解到这个由流域六国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上世纪70年代成立以后,制定了许多控制污染、改善生态的法规,而秘书长一直由地处最下游的荷兰人担任。最下游的国家荷兰在这个委员会里拥有额外的“权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下游百姓的权益能得到充分保障时,上游的问题肯定已经解决。一位长期在西欧工作的河流专家告诉我们,“这里实施的零排放是真正的零排放,三十多年的坚持换回了今天的碧水蓝天。”这不仅在生态上合算的,经济上显然也是合算的,看看满船的游客、河岸上无数的房车宿营就可以知道。 退田还湖与拦海大坝据说荷兰起源于德国一位皇族的流放。这位失势的王公被发配到莱茵河下游,这是当时德国谈之色变的瘟疫之地,到处是水洼、沼泽、泥塘、坑潭。这位君主和臣民们励精图治,一起填补坑洼的地面,一起挖掘纵横的运河,一起疏通满溢的河道,还发明了风车,将水一勺勺舀回大海,以保持土地适于居住与耕种。难怪荷兰有一句谚语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荷兰却是荷兰人创造的。”在荷兰行走,感觉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像。同样是面积广阔的围垦,不过除了围湖造田,荷兰更多的是围海;同样是频繁的水灾,据专家统计洪水的发生率,中国、荷兰正好居世界一、二位;同样靠坚固的堤防来维持着平原富裕地区的安全,以致英语中“垸子(polder)”这个词都直接抄自荷兰语,而荷兰最大的垸子能达到五万公顷;同样与河流不屈不挠地搏斗,在控制河流的同时却也伴生了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80年代起,荷兰就开始大规模的“退田还湖”工程。在荷兰,关于退田还湖还海的争议,发展至极致的是拦海大坝存废之争。拦海大坝主要有北部的须德海工程和西南部的莱茵河三角洲工程。自13世纪荷兰人就开始这项庞大的工程,但主要还是完成于工业化时代。位于莱茵河、马斯河、斯凯尔德河三河交汇入海处的三角洲工程主要用于防止洪水及海水倒灌,工程于年动工,年正式启用,耗资余亿荷兰盾。在东斯海尔德海湾完成了长米的拦水坝,在鹿特丹港的入口处建成了能封住米宽水道、经受住3.5万吨水压的可移动式防洪大坝。拦海大坝曾被认为荷兰人安危所系的“长城”,为何今天又有许多人甘愿“自毁长城”呢?世界自然基金会荷兰分会的河流专家林登杨(LeendeJong)先生却自有一番说法。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期的研究,拦海大坝修建之后停止了莱茵河等多条河流三角洲的发育,反而加速了海岸侵蚀;同时,大坝摧毁了滨海湿地的生态系统,渔业承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沿海许多渔业社区走向崩溃。与拦海大坝一起,荷兰庞大的防洪系统却日益加剧了洪灾的发生,因为人类夺地太多,莱茵河上游的来水无处可以渲泄,最后只能突出堤坝的重围,造成对人类的一次次报复。林先生最后说,他深信,荷兰的拦海大坝“在几十年内定会被拆除”,因为这些“生态后果只能通过向自然妥协来解决”。随后,我们在耐梅亨市参观的一个退田还湖工程似乎印证了林先生的预言。这个项目区位于莱茵河的分岔处,是下莱茵河、瓦尔河和艾瑟尔河汇集的地方。年,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在这里买下了17公顷土地,作为示范区的起步。目前,这块呈三角形楔入水中的示范区面积已经达到公顷,原先的防洪堤坝被逐段后移几百米,建成了一个植被繁密、野生动物出没的生态家园。当然给洪水更多的空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大堤后移。当地保护人士亨利博士强调,在大堤后移之后,还需要恢复河道原有的生态系统,使其充分发挥各项功能,这才是“生命河流”的关键所在。人类在河道两岸修筑堤防,是为了防洪。但实际上,人们应当改变对洪水的观念。汹涌奔腾的洪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让河水白白流走,岂不可惜。为了大堤后移,就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耕地,但同时退田还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湿地产品”,比如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动物,比如河道两岸的自然景观也吸引了众多的大自然爱好者和旅游者,而最重要的“平衡点”却是莱茵河水中的泥沙。亨利先生介绍,粘土是制砖的主要原料,在荷兰属于稀缺资源,而莱茵河泥沙在河道里却淤积成大量的粘土。粘土出售的收入大部分返还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小部分用地大堤后移的工程开支。 从瑞士到荷兰,从阿尔卑斯到北海,十几天里沿莱茵河走马观花,却也天天都能观到美丽的“奇葩”。但是,我们要注意是这些都是先工业化国家用巨大的教训累积的,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的参观者往往只见到表面的繁荣,却忽略了那些失去并且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美丽。 返回顶部 白癜风有什么偏方西安最好的白癜风医院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ylinedu.com/dsjs/7973.html |
莱茵河生态行记
发布时间:2017-6-12 15:07:45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6收关站速降徒步亲子乐
- 下一篇文章: 被时间遗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