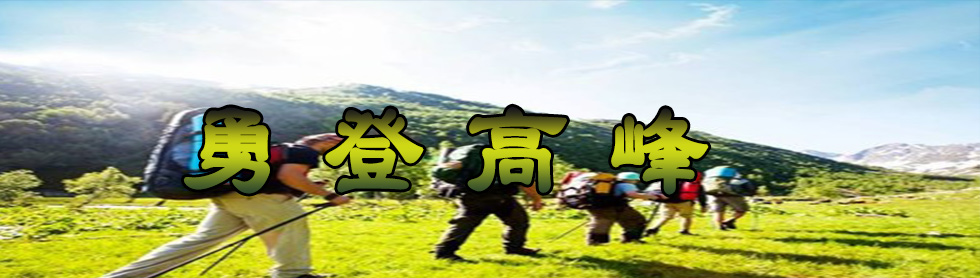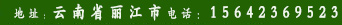|
我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没有名师传授,只是在爷爷的指导之下,从身边的一草一木开始,慢慢了解中医,认知中医,培养了对中医的兴趣。爷爷:民间中医的热忱说起与中医的缘,便勾起了许多孩童时候的回忆,我对中医也并非一见钟情,我也是在一次次亲眼目睹和体验中医的疗效中慢慢爱上中医。我出生于粤西农村,爷爷是搞跌打的民间中医,读书不多,没有系统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常常能够使用一些单方、验方屡取奇效,跌打草药专方更是堪称神奇,救治了许多骨折、筋骨损失的患者,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实实在在的疗效。爷爷是我中医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他是个朴素憨实的地道农夫,一辈子只愿和田地打交道,搞跌打只是他的副业,每当有骨折或筋骨损伤的病人上门求治,他也甚是乐于帮忙。即使70多岁的身子已不再硬朗,他也愿意独自一个人踩着单车去远处的山上采药,每次都需要顶着烈日在山上奔波整整一天,采药回来刚放下碗筷,就又要开始加工草药,单是把一麻袋的树根(跌打类的草药多以根茎入药)剁细碎已经够他忙到深夜里,后面的草药过筛和煎炒也是很耗精力,他却从没说过半个累字,这就是出生于革命年代吃惯了苦头却仍乐于助人的老一辈,这些情景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令我甚是钦佩。(爷爷采药的背影)老中医:传承的遗憾爷爷的医术是受传于她妹妹丈夫的父亲(也就是我姑公的父亲),叫罗田桂(没记错的话),曾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据爷爷口述,罗老先生出生于医学世家,天资聪颖,从小深得家传,知识渊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对风水易学、生辰八字也是了如指掌,在当地很受人尊重。罗老先生看我爷爷为人老实善良,便在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时常带上他去野外采药,一来有个伴互相照应,二来可以亲自教授一些中草药知识,慢慢地我爷爷也积累了许多单方、验方的使用经验。罗老先生也曾经有意收我爷爷为关门弟子,但我爷爷读书不多,自认没有学医的天赋,心里也惦记着家里那一分几亩田,便没答应。对此,我也是深感遗憾,如果爷爷也能成为名医,估计我现在的中医路便不会走得像如今这样迷茫了,不过这都是天意,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在登山路上)虽说没能成为他的徒弟,但是罗老先生还是很无私地给爷爷传授医学知识,爷爷也着重学会了正骨手法和跌打专方,毕竟他认为这个比较容易学而且实用性强。罗老先生的子女也是读书不多,不愿从医,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姑公)对风水易学较为感兴趣,于是就把老先生这门绝活继承了下来,现在对易学这方面也是有很深的造诣。虽说他不愿从医,但从小在老先生的耳濡目染下,他的中医基础理论也是非常的扎实,中医的基本歌诀随口就能背诵,他不愿从医,我也同样替他惋惜,罗老先生的医术就这样失去了继承。后来罗老先生过世的时候,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医书和个人临床经验、诊疗记录等等,可惜后来姑公家里盖新楼房的时候丢失了。那时候我才几岁,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想我要是再早几年出生该多好啊,这是一笔多么宝贵多么难得的财富,唉,人生总难免有些许遗憾。我:爱上中药后来,我在爷爷的言传身授下,跟着爷爷上山下田采药,我从身边的一草一花一木开始慢慢接触中医,听着爷爷讲他一路走来的故事,走着爷爷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山路,渐渐地也积累了许多民间中草药知识。(独辟路径)比如割到手流血了会知道跑去路边采点野草止血;风寒流鼻涕了会知道去摘点紫苏叶再拍点生姜热粥冲服,越辣越好,因为越辣越利于发汗,出点汗感冒就好了;打球扭伤脚踝就知道自己去采点早禾木叶(当地一种草药,具体书名我至今还没法查得到,这个药我后面的文章会详细介绍)来烧热熨烫患处,马上就能消肿止痛。也就这样,我开始慢慢爱上了中草药,爱上了中医,暂且不用科不科学来衡量这一切,但这都是确确实实有效果,疗效就是真理,不是吗?总的来说,我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没有名师传授,只是在爷爷的引导之下,从身边的一草一木开始,慢慢了解中医,认知中医,培养了对中医的兴趣。兴趣才是每个人的人生导师,这也许就是我和中医缘分的开始。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ylinedu.com/dszeb/15665.html |
我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发布时间:2024/5/28 10:24:55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我尝到了运动的甜头我运动我快乐人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