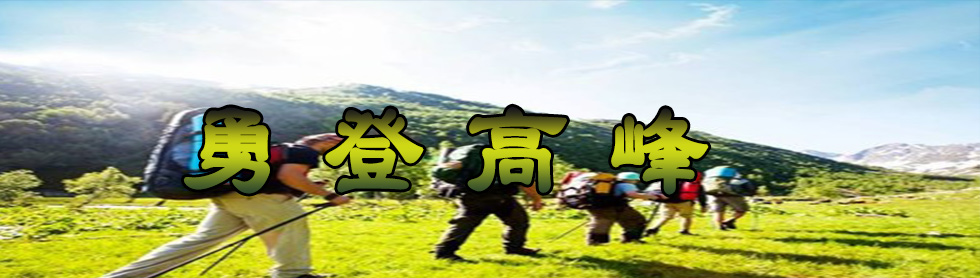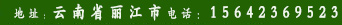|
防治白癜风 http://www.wzqsyl.com/m/永嘉石门台,久闻其名。它不但以楠溪江大若岩景区一谷九漈的瀑布群闻名,更因为它可能与谢灵运石门有关而闻名。自然之秀美与人文之奥妙,自有挡不住的诱惑。六月初,遂呼朋唤友,直奔石门台而去。九漈高入云永嘉游石门石门台,位于大若岩陶公洞附近。陶公洞,于我有特别的渊源,我的永嘉地质科普游和人文地理游,就缘起于陶公洞。殊料,从此就与永嘉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还应邀成为《楠溪江周末》“永嘉风物”的专栏作者,以一个初入斯境者的眼光,对已为人熟知、熟视的永嘉人文风土作一番“胡”说式解读。所以,虽是初探石门台,但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心仪已久。景点入口门额上的“石门台”三字,是启功先生的墨迹,“书贵瘦硬方通神”(杜甫)。登山伊始,即见一座颇有古意的“听瀑亭”,亭柱上有两副对联,一副是启功题写的:“四围山色听飞瀑,千步云阶觅石门”。听飞瀑,觅石门,正合我们此行的目的,在观瀑之余,寻觅谢灵运诗文中反复提及的石门的印迹。另一副,是永嘉文化界谷尚宝和谷胡方父子合作的篆书联:鸟语啁啾鸣翠谷,山花烂漫烨青峦。九漈石门台,以溪谷瀑布群闻名,这里的“九”,并非虚指数量之多,而是实指九条瀑布。永嘉人很实在,九漈,是实打实的九条瀑布,而且只多不少。因为在九漈之上,还有一条源自“云端”的十漈,从高高的山崖上倾泻而下。“漈者,趋下而不回也”,漈,方言字,指瀑布,本流行于浙南闽北,因朱自清的散文永嘉《白水漈》,令天南地北的游客,都知道漈就是瀑布,倒也省却了解释。不过,漈字虽好认,却难写,故常以同音的“际”字替代,甚至再简化为方言近音的“占”字,如当年石门瀑布所在的永嘉黄田东漈岙,也叫东占岙。只是景区树立的公告牌,将“九漈”直接从俗为“九际”,看上去总有点怪怪的感觉。我们沿着景区的石道,拾级而上,不断有不同大小,不同落差、不同形状的瀑布映入眼帘,虽然单条的瀑布规模不是很大,比不上蓬溪的大碏门瀑布,但在三公里长的同一条峡谷中,断续发育了九条瀑布,确是罕见,而且除了第三漈以外,全是天然的瀑布。在这炎炎夏日,看着清澈的水幕,从悬崖上飞泄而下,水花四溅,水声震耳,顿感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在第七漈下停留的时间最长。瀑布旁边有一座石亭,叫“积翠亭”,石柱上还有长长的对联,可惜没记全。石柱就地取材,是火山凝灰岩条石,旁边的岩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岩石的岩性特征,尤其是其中的浆屑,非常醒目,并作半定向分布。所谓的浆屑,就是火山喷发时,尚未凝固的岩浆,被喷到空中时,因发生撕裂而成碎片状、丝条状,在半凝固状态下,又落入火山灰之中,所以特别显眼,其排布方向,代表了火山岩层的层理产状。奔涌的溪水和岩石的立方体节理从积翠亭下望,瀑布溅起的水雾,折射出太阳的七色光,在水潭上方形成一弯淡淡的、小小的彩虹,长不足三米,这应属最小的彩虹了。溪谷是河流的源头,乱石堆叠,但在瀑底的水潭边,却是分选很好的细粒砾石,犹如下游的河漫滩沉积,足见瀑布冲刷的水动力能量很大,对块石的磨砺之功不亚于河流对砾石的长距离搬运。瀑底彩虹和分选良好的砾石石门台山谷,是一条断层带,山涧旁边的火山岩岩壁,往往铁染氧化成红色,而且劈理发育,密集而陡峭。溪谷中致密的块石,或呈立方体节理。分布不均的断层崖造就了多级跌水,从而形成九漈瀑布群,成为楠溪江风景点中独特的地貌景观类型。但令人不解的是,石门台景区明明以瀑布群见长,为什么不叫九漈飞瀑之类的名字,而偏偏要叫“名不副实”的石门台呢?因为所谓的石门台,仅仅是第九漈下面一个微不足道的拱形岩石,比我们想象中的石门台差得太远,即不像门,也不成台。避实就虚,将景点称之为石门台,也许只是因为谢灵运的永嘉石门。李白成就了永嘉石门的文学性符号永嘉太守、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对石门情有独钟,不但有三首诗以石门为题:《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和《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而且还在其专著《游名山志》中详述了石门的地貌特点:“石门山,两岩间微有门形,故以为称。瀑布飞泻,丹翠交曜”。那么,谢灵运诗文中的石门到底在哪里呢?就是石门台吗?谢灵运成就了山水诗,永嘉的山水也成就了谢灵运,正如夏妍在最近一期《瓯风》上著文所说的:“在文学性的社会中,这样的诗文与山水、谢灵运与永嘉之间,自然就画上了文学的等号”。而唐诗则将谢灵运符号化以象征永嘉、象征温州。虽然对谢灵运哪几首诗是专门描述永嘉风光的,众说纷纭,但其中的《石室山》,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说的就是大若岩的陶公洞。既然谢灵运到过陶公洞,那么,顺便登临近在咫尺的石门台,从情理上也说得过去,更何况作为石门山标配的瀑布、丹崖,石门台也都具备。因此,石门台有理由成为谢灵运永嘉石门的候选景点。不过,在历史地理上,最有望是谢灵运永嘉石门的还应是前述的东漈岙,当地有石门寺、石门漈,清光绪《永嘉县志》和千石王氏宗谱就载有多首咏此谢灵运石门的诗。我也曾推测谢灵运后裔聚集地、蓬溪瀑布也许与谢灵运石门有关,但也有人说石门瀑布是指瓯北的白水漈,而周元臻则著文详细论证了谢灵运笔下的石门,就在永嘉陡门村的石门岩。青田、嵊州和新昌等地也都是谢灵运石门的热门竞争地,甚至远在东北大连的一处叫石门的地方,也遐想着若谢灵运来过,那该多好。可见,石门已与谢灵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永嘉山水诗、永嘉石门,都指向了谢灵运。毕竟历史名人的行踪,对旅游业来说,是不可取代之人文资源和文化名片。我觉得,谢灵运游过的石门究竟在哪里,虽无定论,学界也会一直争论下去,但丝毫不影响各地借此进行旅游宣传,同样也丝毫不影响永嘉石门的文学地位。因为早在盛唐时期,谢灵运的骨灰级粉丝、大诗人李白就已经为谢灵运的石门,贴上了永嘉的标签。在唐代以前,谢灵运并不出名,也没有成为永嘉符号,所以无论《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还是《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中,谢灵运都不起眼,也没人将他与永嘉和永嘉的山水诗联系在一起。如同为南朝人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只称谢灵运为临川太守而不提永嘉太守。谢灵运山水诗鼻祖的文学地位,主要是唐诗塑造起来的,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晚唐,张子容、齐己、皎然、李嘉佑、杜甫、朱庆馀、顾况、刘禹锡等等,纷纷在唐诗中以谢灵运象征永嘉并感喟谢灵运的山水诗、畅想谢灵运的行迹,乃至借谢诗宣泄情愁,从而将谢灵运符号化以象征永嘉、温州,而其中居功至伟者当属诗仙李白。李白在《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的开篇,就掷地有声地宣布:“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他的另一首《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的序言也明白无误地指出:“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从而夯实了谢灵运成为永嘉符号的基石,同时也完成了对谢灵运永嘉石门的文学性认定。如果将李白的诗改写为:康乐上官去,始宁游石门或青田游石门、嵊县游石门,则诗意和诗味就荡然无存了,也不会有后来众多的诗人,受其诗歌的影响,到永嘉、到“谢客郡”追寻谢公的履迹了。南朝《谢灵运集》,早在北宋时就散佚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谢灵运山水诗,主要是明中期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李梦阳(-)辑佚的结果,并刊于《古诗纪》和《谢康乐集》。换言之,李白的千古名句“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底气足足,言之凿凿,因为李白与他的偶像毕竟只相隔了区区三百多年。所以,永嘉石门作为文学性符号,是无处可及,也无人能够撼动和更改的。“永嘉游石门”,是永嘉山水诗和谢灵运作为永嘉符号的重要内容,也是永嘉游的一张共享文化名片。来源/中国永嘉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ylinedu.com/dsjs/15479.html |
李白诗中描述了永嘉游石门,这个石门到
发布时间:2024/3/23 13:22:59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来来来,一起去嵩山少林学武功才不是,这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